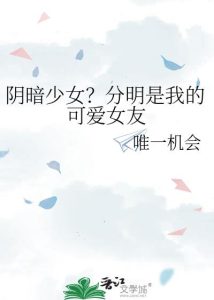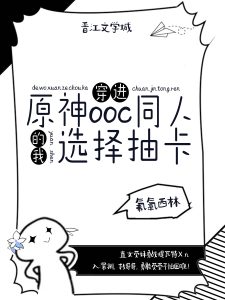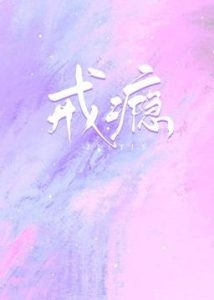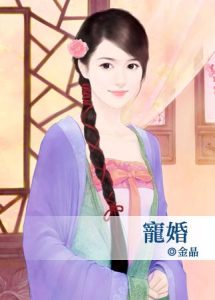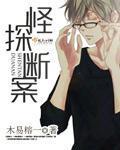第 237 章 金沙舊事
“本想試着再查到一些線索,結果徒勞無獲,又恰巧叔公尋去,便放棄尋查,趕回偏堂寫結案折子了。”
“這麽說……你此時對朕說的東西,只有你一人知曉?”趙惇再次确問。
“是,草民将此事帶到延和殿與陛下詳談,陛下應知草民是知輕重之人。”
“哼!你知道輕重?你敢跟朕論及此事,真不怕掉腦袋!”
韓致遠身上那種淡定不懼令趙惇心慌又羨慕。
身為一朝皇帝,當了快二十年的太子韬光養晦,他都無法做到像這個年輕人這般從容不迫。韓致遠越是面色平靜無波,越讓他覺得是在看自己的笑話,失了身為天子的自信。
這,讓他很想将這顆腦袋砍掉!
可是偏偏,殺不得。如今大宋這樣的可用之人不多,他需要這樣的人為他清理障礙,可是不希望最終清理到了他自己的頭上。
“如果陛下以為,靠這場肅清整頓能夠永除後患,草民破獲這樁案子便算是功成名就,死而無憾。”
這便是韓致遠的回答,他的底氣在于,他知道自己的價值,知道皇帝要殺他的猶豫。
他清楚的知道,他為大宋的安危付出那麽多,被人當做大宋的一把利刃,說到底也是屬于皇帝的利刃。
他不滿如今的當權者,可是為了偏安一隅的大宋能夠在風雨中堅守下去,博得一線喘息的機會,有朝一日能夠龍騰翻身,如今的當權者已經坐在那裏,便不能動搖,依靠其飄飄欲墜的皇威,一定要堅持到……有位明主上位。
趙惇抵靠在椅背上,動怒、心驚之餘是疲憊、無奈,可又不想失了身為皇帝的氣勢,“既然你沒完沒了的這麽難纏,朕可以滿足你的好奇心。但是為此,你要付出代價。”
“請陛下明述。”韓致遠做好了洗耳恭聽的準備。
趙惇朝張成和揮揮手。
正在捶背的張成和停手退到一邊。
“朕知道,像你們這些耳聰目明的家夥肯定私底下會聽到一些事兒,可又怎樣?誰敢無憑無據地跑到朕跟前質問?除了你,韓致遠,除了你!逼到朕面前,要朕親口對你吐出真相,那些陳年舊事已經過去二十三年,那個時候你都還沒有出世!”
“陛下認為受草民逼迫,只因恰是草民插手了這個案子。如今真正逼迫到陛下的不是草民,而是他。”韓致遠低頭,指肚正壓在紙條上的那個身着通天冠服的小人旁邊。
這個小人兒指的是原本皇帝該躺在那個位置,還是指的已故莊文太子應該着皇帝朝服?
“不,皇兄不會逼朕,不會的!”趙惇盯着韓致遠手中的紙條,“皇兄非常愛護朕與明王兩位皇弟,他走的那般安詳,沒有帶任何怨氣。只是朕到現在也不明白,皇兄當年究竟在做什麽!”
……
“那一年,就是乾道三年中元節剛過,朕與大皇兄同游浙江,經過金沙渡的時候确實是發生了一點兒意外,可并不是有些人認為的那樣,懷疑什麽是朕趁機謀害皇兄!簡直無稽之談!朕與皇兄可是親兄弟,又欽佩其學識能力,視其為榜樣,怎麽會想要害他?”
“當時朕提議飲酒,不過是怡情自樂。平時出游,朕都喜歡帶幾壇子老酒,泛舟小飲吟詩賞景,那是別有一番樂趣。可誰想,這剩下的最後一壇酒會有問題!朕喝了小兩杯就不省人事,醒來之後,只有成和陪朕在岸上。是成和告訴朕,皇兄将朕送上岸,要成和陪護朕,然後乘船離開,說是讓朕在岸邊等着,他很快就會返回,至于去了哪裏,朕無從得知,成和也沒資格過問。”
“果然,黃昏時分,皇兄就回來了,船夫都是他的人,沒人會對朕多說什麽,皇兄對此行也三緘其口,他要朕當做什麽也沒發生,可朕見他渾身都濕透,像是落水的樣子,定是發生了什麽事,可他不肯說,朕也無可奈何。”
“後來,皇兄回到皇城沒多久就生了病,太醫初診說是着了江水得了風寒之症,可是高燒遲遲不退,伴有痙攣,後太醫再細致查問方知大皇兄的腳上曾碰傷,一直未愈,又受邪風侵入,是患了惡症破傷風。此症在我朝《太平聖惠方》中有載,你也可以去問吳誠儒,這個病在初期藏于人體內,不易察覺,待症狀發作明顯時就十分嚴重了!”
“當時太上皇招齊太醫局全部太醫為大皇兄診治,皇兄不僅沒有好轉,反而病的越來越重,只撐了三日便……為此,太上皇遷怒太醫局。或許是為了推卸責任,或許是為了給出一個說法,太醫局認定是那個主治太醫下錯了藥量,那名太醫被斬殺,卻也連累了朕,繼皇兄在金沙渡受朕毒害傳言之後,又有人暗中揣測,說是朕借太醫之手,要了皇兄的性命!只因朕被封為皇太子,取代了皇兄,就讓朕來背這個黑鍋!朕是多麽冤屈,當年若是有你,朕定讓你将此事查個水落石出!”
“當然,當年即使沒有你韓致遠,朕也是要查的。可這是大皇兄做的‘案子’,怎麽查?朕在大皇兄面前向來自愧不如,如何能破的了大皇兄的局?金沙渡一事,朕知道,大皇兄的身上藏着秘密。他至死都不願讓朕知道,可是關系到朕的清白,關系到衆人眼中朕與大皇兄的兄弟之情,在他不清不白的病逝之後,朕怎能不追查?”
“朕決定查問當時在金沙渡的那四個曾随大皇兄離開的船夫,結果那四名船夫全部先朕一步被綁架,綁架的地方就是在艮山月老祠的後山。朕與張成和率人依線索尋去,還是晚了一步,那四人全部被殺,都死在朕的眼前!當時朕有多震驚,你知道嗎?”
“偏偏在那個時候,有人趕到,朕以為他們就是綁匪,命張成和率衆人做好應對準備,可誰知他們都是太子舊部,不知從哪兒收到消息恰巧趕到艮山,看到當時的情形,不論朕怎樣解釋,他們都認定是朕殺人滅口,并且在他們看來更加印證了莊文太子的死與朕有關。可滅口之人不是朕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