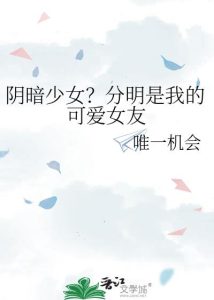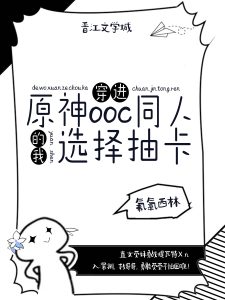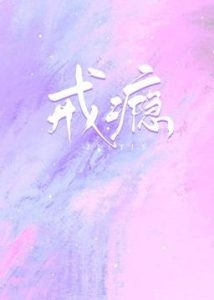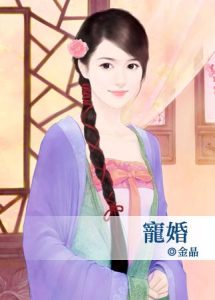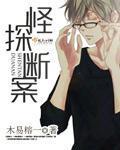第 238 章 盤花紋印
“當時那種混亂之下,一個個恨不得将朕捆縛押送到太上皇面前,恨不得帶着朕游街示衆,恨不得讓朕為大皇兄去陪葬!朕怎麽辦?滿口說不清的朕該怎麽辦?”
“所以,陛下就把所有人都殺了。”韓致遠道。
聽皇帝講到這裏,他聽了滿耳朵的冤氣,也聽出了隐在冤氣之下的殺意。
這樣的心性,與陳立等那幫信奉“上神”,推崇以案制案去讨要“公道”的人相比,有什麽不同?
毫無章法,只圖一時之快,枉顧無辜者性命!
這種人,還能說他含冤不白嗎?這些人,不論打出怎樣正義的旗號,都掩不住已經惡變的內心,改變不了已經成為罪人的事實。
而這個人,是當今大宋的皇帝!
趙惇伸指點點韓致遠,“你想到了,換做是你,你是不是也只能這麽做?”
不會。
韓致遠只是在心裏回答。他此時不想跟皇帝因這個問題争辯什麽,他要聽皇帝繼續說下去。
“是!朕殺了他們!”趙惇親口承認。
承認一件在心底壓了許多年的秘密,反而有輕松暢快之感,“三人成虎,他們不止三人!他們都認定朕是兇手,朕又被人算計無法證明清白,那麽就只能讓他們跟那四名船夫一樣,一起被滅口,才能求個幹淨,才能不讓奸人的陰謀得逞!于是,朕給張成和下了殺令。既然他們都心系皇兄,與其淪為被奸人利用的工具,對付朕,不如讓他們去為皇兄陪葬好了!”
“陛下下手的時候,就沒想到,如果那個時候再來一批人,可就是親眼看到陛下在率人動手行兇了。”韓致遠道。
沒有行兇,仗着身心坦蕩,還有辯解的機會,親手行兇又被人看到,那就成了無從狡辯名副其實的兇手。
“是,朕沒想到。朕承認當時是被他們一口一個質問給氣瘋了,沒有想到那麽多。”
趙惇的言語間并未透出多少悔意,冤氣難消,依舊在遷怒那些已經死在他手中的人。
反而是張成和,追悔不已,跪倒在地,“不,官家,是小人沒有盡到照顧陛下的責任,是小人失職,沒有提醒陛下,致使陛下釀成大錯,該擔此責任的是小人!”
至誠至懇,聲淚俱下。
“罷了,你對朕一向忠心,聽命于朕,怪不得你。”趙惇擺擺手,繼續道,“沒錯,就在朕下令殺掉那幾個人的時候,又來了一批人。當時朕又驚又怕,意識到自己掉進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中,只能放手一搏,或者同歸于盡,或者殺出重圍,或者成為對方的刀下野鬼,但不論結果怎樣,艮山就是朕不得不面對的戰場!”
趙惇談起那場殺戮是大氣泠然之色,“朕的人是那般骁勇善戰,沒用多久就将所有人全部斬殺。有人想利用他們指證朕,可他低估了朕的當機立斷!所有人都死在刀劍之下,那片山坡都被血水染紅,遍野橫屍。看着眼前的那一切,朕冷靜下來,一時不知該如何處理這麽多屍首?在那個時候,朕竟有了種錯覺,好像大皇兄就是死在朕的手中,否則朕為什麽要殺這麽多人?朕一定是瘋了!”
“所以,當年陛下在艮山遇刺一事并非陛下真的遇刺,只是陛下為了遮掩這場殺戮的真相。當年就有人懷疑是陛下使用的苦肉計,流傳出對陛下不利的言論,但陛下身負重傷,性命垂危,太上皇與高宗皇帝都不相信,只認為是有心人故意散播的傳言。”韓致遠說出一段衆人所知的過往。
作為後生晚輩,他從沒有主動去探究那段過去,若非剛破獲的這樁案子與之相關,他也不會沒事找事的去揭開這道塵封已久的醜陋疤痕,他從來沒有把艮山的問題引到皇帝身上,是那道突然而至的聖旨讓他聽到了皇帝心虛的聲音。
現在,他明白了,皇帝是怕被那些冤魂打擾。張路縱火燒山順帶想要他的命,其實也是為了震懾皇帝。那漫山的綠色鬼火傳到皇帝耳中,一定令其極為驚駭。這便是慕清顏在山洞中聽到李慶與陳秀娘所說的,燒山的另一層意圖,他們通過這種隐射的手段對皇帝隔空敲打,如一把無形的劍劃傷皇帝的心神。
“是,面對那麽多具屍首,朕想到了自殘,朕就是受害者,怎麽會是兇手?所以朕拔劍砍傷了自己,讓成和等人将朕救回宮,那些死掉的人全部都是刺客,他們死有餘辜!為此,太上皇下令,徹查莊文太子舊部,警告任何人不得利用已故莊文太子與他的皇子們做文章,挑撥生事。為防被冠以結黨營私的罪名,與莊文太子交好的舊人全部散開,各奔東西。朕之後的路都是朕拿命博得的,足足五劍,兩劍在腿上,三劍都在上身,其中一劍離心口只有兩寸!若非朕對自己下了這般狠手,艮山的麻煩還不知該如何收場!這一招絕對是暗中引事之人始料未及的。”
趙惇說到此,眉眼含笑,顯出幾分洋洋得意,當年的那件血案不僅未令其痛心,反而被他當成引以為豪的壯舉。
韓致遠低垂下眼睑,陛下聖明這句話,他無論如何吐不出口。
那些被殺死在艮山的人,不僅死的很無辜,還擔上了刺客的罪名,致使他們的家人後代都活在不明不白的恥辱之中,而這,只不過是這位皇帝為求自救的一招。
“不論真相如何,莊文太子已故,身為父親的太上皇是不願看到再有兒子離去的,所以他必然會保陛下。”韓致遠道。
其實,不能說皇帝幾近瘋狂的苦肉計有多高明,只能說是太上皇與高宗皇帝不願讓此事成為趙氏醜聞被揭開,一個皇子已經死了,哪怕那個皇子身邊的人有多麽不滿,哪怕這個皇子身上有多少疑點;哪怕曾經他們都多看好那個皇子,哪怕實際上他們很明白這個皇子的心性,他們都只會将此案壓下,絕不會再用一個皇子的死去彌補已經死去的那一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