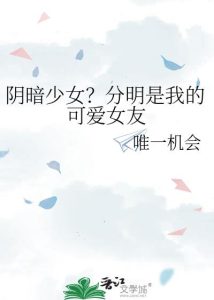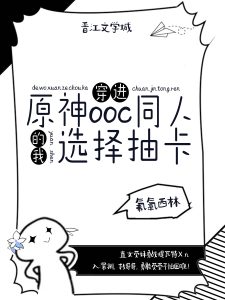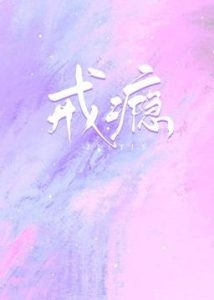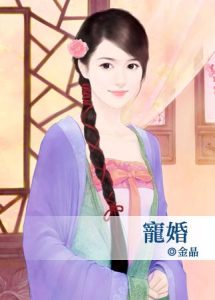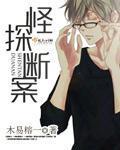第 451 章 漳州傳說
主簿一驚,“哦?竟有此事?那得即刻将那個冒牌張路捉拿,便能審出真正張路的下落。”
朱熹比主簿鎮定,“你并未見過其人,怎能肯定是有人冒充張路,而不是張路本人?”
“朱大人認為,這個張路可會是行兇作惡之人?”慕清顏指手中文書。
“若從其母身上看,不像。”朱熹略想了想。
“是不是去找那個張路來看看不是便知?”主簿道。
慕清顏道:“太學生張路兩年前就已經退離太學,且死于上個月,三月十五夜。死前曾參與臨安謠言案,并直接誘拐謀害無辜女子。還有,韓公子讓大人看的那封信就是出自太學生張路之手。”
慕清顏解下背上的包袱,從中翻出一張畫像。這張畫像出自留小婉之手,是韓致遠經過艮山火險之後,找留小婉到刑部偏堂依他描述,畫出的縱火兇手樣貌。之後,韓致遠帶這張畫像到太學,被太學生們認出此人不是王坤而是張路。
“這就是那個太學生張路的畫像。”慕清顏将畫像遞給朱熹,“不需見到死者,只要讓那位尋子婆婆辨認這張畫像便可。”
剛才她聽聞那個婆婆的兒子叫張路,而且尋找了三年多,腦中第一冒出的想法便是此張路非彼張路,也就沒想到讓其确認畫像。現在朱熹與主簿都問起,為有完全證實,便還是免不了這一步。
其實,太學生張路為非作案,又恰巧失了具體身份備錄,這個鄉下婆婆苦苦尋找兒子三年之久,出身寫的明明白白,誰是誰非已經自見分曉。
“去問問。”朱熹将畫像交給主簿。
待主簿拿着畫像離開之後,朱熹又道,“真沒想到,一個人口失蹤案會與你們來漳州的目的有所牽連。”
“朱大人,您可知登高山上那兩塊迎客石的傳說?”慕清顏問。
“約百年前,妖眼作惡,被開元寺一得大師取天寶山兩塊柱形大石封壓?”
“正是,四娘給我簡單講過。”
“老夫所知并不比你從何四娘那裏聽到的多多少。關于迎客石傳聞都是漳州百姓多年來口口相傳,另外便是開元寺一得大師舍利塔碑文所留。當年真相如何無從知曉,不過妖言惑衆之類的言論豈可偏信?”
“舍利塔碑文怎麽說?”
“老夫自到漳州上任,并未踏入開元寺的門,開元寺碑文內容由主簿謄抄。上面寫的大意是,崇寧元年,登高山姐妹泉眼突然染毒,有附近登山打水的人因飲用皆中毒而亡,同時,就像如今這般,死了一片老鼠。當時的泉眼所在亭臺并未像今日這般整修,石壁也并未特意開鑿,死去的老鼠順着坡勢滾落,據說數量非常多,引起衆人驚恐。”
“住持高僧一得大師誦經為亡靈超度,舉辦法事,讓人從天寶山采來兩塊石頭壓住了泉眼,并以泥堵住縫隙,阻止泉水冒出,此事被說成那兩個泉眼是被鼠妖毀壞,一得大師擁有鎮妖功力。不久之後一得大師圓寂,據說是因行法力傷了身體。其舍利便被供奉在開元寺,得後人瞻仰祭拜。此後,又有善人将平臺修整,鑿開石壁,建造了一處亭臺,但因不想提到妖孽這種字,便沒有把那兩塊石頭叫做鎮妖石,而是稱之為美名迎客石,但在龍溪縣的人心裏,祖祖輩輩都将其當做鎮妖石,甚至無人敢在石上亂塗亂畫,幹幹淨淨保存至今。而開元寺從此被衆人極為供奉,尤其近些年,連官府的香火錢都一起收!”
……
慕清顏一時間算不清年時,“崇寧元年?那是……”
“距今八十八年,徽宗年號。”朱熹對此算得清楚。
“也就是八十八年前的事?好好的泉眼不能飲用,毒死人還有老鼠?開元寺僧人處理此事,難道在那個時候開元寺的僧人就與其他寺院不同?”慕清顏問。
朱熹搖搖頭,“老夫幼時便在家鄉尤溪縣聽聞過登高山的這一傳說,一得大師在漳州流傳下來各種濟世為民的事跡幾乎傳遍福建路,也曾到各地宣講佛法,其修行有口皆碑。能留給後人這般聲名,不是靠行瞞天過海之術能夠做到。開元寺當年的傳說應該與現在的這些駐守在寺中的棍僧應該無關,而且此事在位于登高山上另外兩大寺院:法濟寺與淨衆寺中也有流傳。雖如今開元寺僞僧行徑漸顯霸道,但那二寺對一得大師也是崇敬有加。”
“老夫以為,八十八年前的事應該另有蹊跷,只是過去已久,無從查起。再說之前老夫也并不以為意,天下各處從不會少了傳說,就像今日之案,不知百年之後又會變成怎樣的說法?”
慕清顏凝眉道:“可是如今,舊事明顯被有心人借用。吳叔叔查驗結果是有人對泉眼冒出的水漬下了毒,致使不知被如何引去的老鼠飲用斃命,也令韓公子與我中了毒氣。可此事在被桂林村失火案,以及玉婷館下現鼠窩等影響到的衆百姓看來卻是妖眼重現,鼠妖橫行,一切責任全部歸為大人!若大人處理不當,更會直接危及到漳州的安穩。”
“這就是案犯的意圖?”朱熹猛然暗驚。
之前,朱熹只是以為頂多是一夥歹徒行兇作案,只是為了逼他停止革新,維護他們互相勾結的利益,而眼下案情的發展卻讓他看到了整個漳州在搖晃!
這根本不是他的過,革新只是被真正的案犯當成了借口,而他到漳州,只是誤撞進了這潭泥穴。
“果然不是張劉氏之子!”主簿拿着畫像返回,“我找張劉氏辨認,張劉氏開口問是為何,絲毫沒有看到她兒子的反應,我只得跟她說是名朝廷通緝犯,請她辨認一下,她便說從未見過此人。”
朱熹從主簿手中拿過畫像,“張路的身份被人冒用,怕是兇多吉少!”
慕清顏道:“可要弄清假冒張路者是何人,還得從追查真正張路的下落查起。”
“張劉氏說張路是去汀州之後杳無音訊,冒充之人想必曾出現在漳州以及附近。老夫着人将此畫像翻畫,着人在各地排查。”朱熹道。